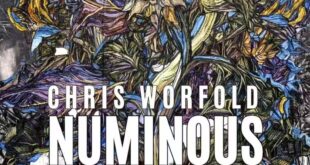斯文与侮辱
一个中国文化世家的传奇
1949年深秋的一天,清华大学英文系教授钱钟书,把大三年级的期末考卷带回家里批改,11岁的女儿钱瑷在旁边给爸爸登分。
突然,钱瑷指着两份卷子说:“这个英若诚跟这个吴世良要好,他们是(男女)朋友!”钱钟书疑惑不解:“你怎么知道的?”钱瑷说:“全班人都是用蓝黑墨水答题,只有他俩用的是紫墨水!”
就这样,英若诚和吴世良的恋情才终于曝光。
对这两个学生,钱钟书都不陌生。
据说,晚年时钱钟书自己说过:全中国真懂英文的,加起来只有两个半,一个我自己,半个是复旦大学的林同济,另一个,是辅仁大学的英千里。——谁都知道,马英九是给蒋经国当英文秘书起家的,他的英文就是英千里先生教出来的。英若诚就是英千里的最钟爱的儿子。

而英千里本人,又出生于一个典型的晚清民国崛起的知识精英家庭:父亲是《大公报》和辅仁大学的创始人;岳父是北洋大学创始人和北洋政府教育部长。

至于吴世良,同样出身民国大知识分子家庭。她的父亲吴保丰先生,是民国初年第一批学成归国的留美学生,中国无线电事业的奠基人,后来长期担任交通大学校长。
英若诚与吴世良的恋爱故事,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精英家庭子弟生活方式与价值观的写照:隐忍、低调、隽永,永远静悄悄却又自有浪漫情致。1950年7月17日,他们在北京结婚。从此以后,这个家庭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下,开始了身不由己的“漂泊”,在斯文与侮辱峰谷之间几经波折,最终不可逆折的走向文化上的败落,成为近代中国文化世家命运的典型样本。
就在英若诚和吴世良相识的前一年,吴家正经历一场巨大的历史考验。这一年夏天,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因为抗议美国石油公司员工撞死中国学生,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交通工程系的同学甚至拆毁了一段沪宁铁路以示抗议。已被震惊全国的“沈崇事件”搞得焦头烂额的蒋总统,大发雷霆,要求校长吴保丰立即前往南京接受训话。
面对震怒的蒋介石,国民党员吴保丰平静地说:委员长,记得1927年北伐的时候,全国的学生和老百姓都向着我们,如今刚刚过去二十年,民心向背天翻地覆,这是到了我们该自己检讨的时候了。
盛怒之下,蒋介石拍着桌子对吴保丰说:你已经老糊涂了,作为交大校长,你的影响太坏!如果十天之后我发现你还在上海,就别怪军统对你不客气!
吴保丰先生是二十世纪第一代留美归国的知识分子,三十年代,在他的擘画下,中国第一个无线广播电台在南京建立。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他为五个孩子分别取名:温、良、恭、俭、让,吴世良是他第二个孩子。然而,就是这样温柔、敦厚、谦虚、静默的学者,在巨大的威权面前,却保持了内而外的风骨和傲气。
在这样家庭里长大的吴世良,终其一生,始终保持着高贵、优雅的文化贵族气质,无论身处优渥抑或身陷囹圄,从未表现出任何自娇自傲或者自艾自怜的态度。
直到临终前,吴世良都在翻译美国华裔女作家包柏漪的名作《春月》。主人公春月,仿佛正是吴世良的化身:隐忍、博学、坚毅;写字、画画、作诗,静悄悄地吃饭……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一个方面。
相比起吴世良,英若诚的家族,更仿佛是一个传奇。这个奇迹的缔造者,是英若诚的爷爷英敛之。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去,这个原名“赫舍里·英华”的满洲正红旗下层武士,都是一个传奇。他只活了58岁,却干了三件大事:一是创办《大公报》;二是创办北京辅仁大学;三是创办香山孤儿院。
1902年,35岁的英敛之创办《大公报》时,曾向读者解释过这三个字的寓意:“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报之命各固已善矣”。自从创办伊始,《大公报》就以“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为宗旨,从创办之初的“提倡变法维新,反对顽固守旧;要求民族独立,反对外来侵略;敢骂酷吏、不避权贵”到四十年代的“不党、不私、不盲、不卖”,《大公报》是中国报人最优秀品质的集中体现。
到了晚年,英敛之深刻意识到“介绍西欧新得科学文化之精”的同时,不能舍弃“中国旧有文学美术之最善者”,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上书罗马教廷,力主在中国开办天主教高等教育学校。
这所大学就是亚洲惟一一所由罗马教廷直接设立的天主教大学:辅仁大学,校名是英敛之取的。他的同道好友,晚年捐资创办上海震旦大学的马相伯曾主张以“本笃”为校名,英敛之坚持取名“辅仁”,典出《论语》中的“会友辅仁”。
对于英家人来说,英敛之的故事太过遥远,他的儿子英千里,才是真正改变了家族命运的人。
辛亥革命以后不久,年仅12岁的英千里就被父亲交给天主教传教士雷鸣远带到英国去学习强国之术,这个举动至今令英家后人啧啧称奇,“英敛之这个人意识太超前了,一百多年前能有这样的眼光、气魄,他可就这么一个儿子。”十二年之后,英千里自欧洲回国成亲。婚后头六年,他仍然生活在欧洲,偶尔回国探望。英敛之意识到,儿子虽精通西学,在全英注册考试中名列第一,拿下了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学位,却连中国字都写不好,中国话都说不利落,更不能指望他干预时政,推进社会变革。这种“追悔莫及”的心态,使他开始重新反思当年“全盘西化”的主张,最终创立了以兼收中西之长为宗旨的辅仁大学。
英敛之亲自帮儿子挑选了妻子——北洋大学创始人、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蔡儒楷的女儿蔡葆真小姐。英若诚后来说,“一个是当时天津唯一一家报纸的社长,一个是当时天津唯一一所大学的校长,这是一桩典型的门当户对的知识分子联姻”。
回国以后,英千里一度同时担任辅仁、北大、北师大三校教授,薪水最多时每月一千块大洋。每月发了薪,孩子们就爬在床上拿大洋当玩具。当时北京城里的福特汽车,不超过二十辆,其中一辆,就属于英千里教授——每到暑假,他就带着全家人去京郊的别墅度假。而平时,他带着一大家子,住在晚清重臣庆亲王奕劻的府邸。
更令人羡慕的,是这个当时的知识精英家庭的民主空气与文化氛围。
母亲蔡葆真奉行“树大自直”的教育理念,给予子女最大的自由空间。父亲英千里即便给他们立规矩,也“总是很绅士”。英千里有三间书房,里面堆满了各种书籍,孩子们从小就在里面胡乱看书。晚上父亲情绪一高,就把孩子们叫去,给他们讲希腊神话,每天都讲一段,《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基本上都讲完了,特别生动,太好玩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英家失去了这份喜乐平静。英千里和辅仁大学的一些爱国人士秘密成立了地下抗日组织“炎武学社”,由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沈兼士任主席,英千里任书记长,直接接受国民政府的指示,在学生中宣传抗日思想,鼓励学生投身抗战。
1941年12月30日,日伪特务翻墙闯进英家,带走了英千里。妻子蔡葆真对12岁的儿子英若诚说,我只担心一件事,抗日积极分子的名单被你父亲夹在一本书里,得在日本人发现之前找到它。
英千里在监狱待了三个月,日本人用尽刑罚,却一无所获。作为在家的长子,英若诚无数次给父亲送吃的,送衣服,他到死都记得父亲在日伪监狱里的编号:770。
1944年,英千里再次被捕,国民政府起初以为他已英勇就义,还在重庆为他举行了追悼会。直到日本投降前两周,他才在社会各界的营救下出狱,一夜之间成为大英雄。
日本投降后,英家做的第一件事,是买了一包绵白糖。整个抗战期间,与绝大多数爱国知识分子一样,英家与祖国同甘苦,共命运,他的几个最小的孩子,甚至没有见过白糖的样子,以为那是雪。
1948年12月,北京已被解放军围城,英千里作为国民党政府“大陆人才抢救计划”中的重要人物和胡适等人从北京东单机场匆匆飞往南京。在此之前,英若诚曾专门从清华大学跑回城里,劝说父亲留下来,不要跟着国民党去台湾。“我的宗教信仰怎么办?”这是英千里最大的担忧。到台湾后,英千里把全部心血投入了教育事业,他除担任台大外文系主任外,还在多所院校任教,并和辅大校友们共同努力,促成辅仁大学在台北市开学。据说,当年台湾地区所有从初中一年级到大学四年级的英文教科书,均出自英千里之手。
在台湾,英千里恪守着天主教徒的生活准则,一生没有另娶。而在海峡的那一边,他的孩子们与他划清界限,放弃了原有的宗教信仰,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却因为家庭出身太差,海外关系复杂,多数被组织拒之门外。
1969年10月8日,英千里因肺癌在台北耕莘医院故去,享年69岁。临终前留下遗嘱,将公教保险费新台币13.8万元全部捐给英氏奖学金基金会,用于嘉奖优秀青年。他的最后一笔款项,永远留给了后人。
直到十年之后,英若诚访美,才从白先勇那里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又过了十四年,英若诚才在父亲学生马英九的帮助下实现了去台湾祭扫先人的愿望。在父亲的墓碑上他看到了父亲的照片,“样子比我记忆中要衰老”。这是他与父亲的最后“团聚”,此后,英若诚的身体状况恶化,再没有踏上台湾的土地。
英若诚这个名字,是父亲当年请史学泰斗陈垣先生取的。当年从天津圣路易中学毕业时,英若诚已经获得免试进入剑桥大学的资格。
英千里与儿子长谈了一次,“当初你爷爷把我送出去,是希望我从小就学习西方文化,从根本上了解西方世界的科技和文明,将来好为自己的国家做事,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造成我一生无法弥补的欠缺。我12岁出国,24岁回来,完全不了解中国社会,很多应该做又很想做的事情都做不了。”他劝儿子以自己为鉴,放弃剑桥,改在国内上大学,“千万不要从一个外国学校出来,再进到另一个外国学校里去。”
英若诚为此放弃了剑桥的入学机会,进入清华大学念英文。毕业以后,因为同样酷爱戏剧,他和妻子吴世良双双进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为院长曹禺先生钟爱的演员和助手。1958年,因为出演老舍先生的名剧《茶馆》里的刘麻子,英若诚一举成名。
改革开放后,英若诚精通的洋文终于派上了正经用场,他结识了美国战后最重要的剧作家阿瑟.米勒(他也是玛丽莲.梦露最后一任丈夫),《推销员之死》、《哗变》、《请君入瓮》、《芭巴拉少校》、《上帝的宠儿》等名作,都是由英若诚翻译、引进到北京人艺的外国戏。
英若诚把自己认为一流的西方大师之作引进到中国,同时也把中国戏剧文化传播到西方。作为密苏里大学的客座教授,他给美国学生排了两部中国话剧,《家》和《十五贯》。他是当时北京人艺海外影响最大的演员之一,《忽必烈》、《末代皇帝》、《小活佛》、《马可·波罗》等影视作品为他赢得了一大批海外观众。
英若诚曾说,“我们提倡爱国主义,首先要让青少年知道中国与世界的现状,加以对比,祖国才可爱。有的人认为应当把中国说成好而又好,革命灯塔、世界乐园、人间天堂,这便是爱国……这种说法太片面,经不起比较和事实的检验,往往连真正的伟大之处,也被后代轻易否定……什么叫爱国?就是‘要在他的领域里赢得他的尊敬!’……世界上什么事都有一套公认的规则,不能关上门老子天下第一”。
1986年,他从一名股级干部一跃成为文化部副部长,主管艺术院团和艺术院校。曹禺送给他一幅字,“大丈夫演好戏当好官,奇君子办实事做真人。”
六十年代的牢狱之灾,是英若诚一生永远的创痛。1952年起,北京市长直接授命他利用自己的海外关系,了解西方动向,为组织搜集情报,他还获准可以阅读大量英文读物。结果,1968年他以“美苏双重特务”的罪名被捕入狱,经过多次审讯,他才意识到自己被捕的真正原因是曾经为那位被打倒的彭市长工作过。
他在北京、河北等几座监狱过了3年牢狱生活,他的妻子吴世良在他被捕的第二天也被抓了。他们16岁的女儿英小乐被送到内蒙古插队,7岁的儿子英达先是跟奶奶生活,后来被迫流浪街头,住在下水道里,在街头要饭吃。在自己最需要模仿学习父母的年龄,英达和他的兄弟姐妹并没有受到他们的影响和教育,这是英若诚一生无法消弭的心灵创伤。

作家“惠说惠道”说她在北京接触了一些世家子弟,心中一直有一个疑问:他们似乎并不是我想像中的那个阶层的人,为什么他们身上似乎没有他们父辈身上那种斯文体面的气质呢?
慢慢地,她找到了答案,“频繁政治运动的冲击,令每一个家庭都受到了不同的伤害,父母忙着搞运动,小孩子是没人教育的。回头看,这些政治运动已严重戕害割裂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和传统,体现在个人家庭生活中的就是即使是世家子弟也全然丧失了温润斯文的气质”。
政治运动对传统文化的冲击超过战争和自然灾害,对家庭成员的伤害更是超过战争和自然灾害。当政治运动来临时,英达的所有亲朋好友都在追求“进步”,努力切断与家庭的纽带,实际上也就隔绝了与家族文化血脉的传承。英达无疑是一个典型代表。
且不说当年他与妻子宋丹丹不惜公开撕破脸皮的争执,就说2017年初媒体重炒旧饭,拿2011年“英达涉洗钱”的旧事炒作——英达和第三任妻子梁欢为了规避美国税务局的监管,多次来往于多家银行,每次存款额度小于1万美元。这种斯文扫地的小里小气,这一个个的英达和我们,构造了当下中国的气质。
如今,英达把梁欢和儿女放到了美国,如很多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一样,他们想找到不浮躁的家庭生活,也想借此治愈自己年少时一人流浪在北京街头时所受的伤害。
只是,文脉断了,还有可能找回来吗?
源自:惠说惠道,2017 年 09 月 30 日
编辑:wouk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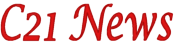 世纪新闻 C21 News Les nouvelles de la Chine et du 21e siècle
世纪新闻 C21 News Les nouvelles de la Chine et du 21e siècle